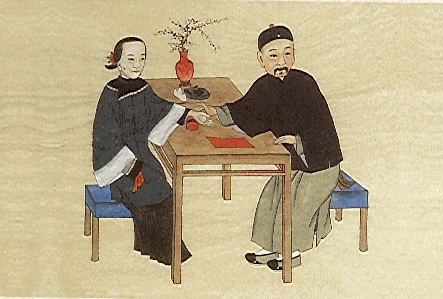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医生。从记事起,我就不喜欢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也很怕打针。好在从小我是一个健康的女孩,很少生病。偶尔感冒咳嗽,奶奶会给我喝一杯姜茶,用毯子裹着我发汗,还用瓷汤勺在背上刮出一道道红的痧印,烧就很神奇地退了。“半夏露”是我最喜欢的咳嗽糖浆,没有生病的时候我常把它们当糖水喝。偶尔犯胃疼,奶奶会拿一个盐砵在我的脐上拔火罐,也很有效哦;我的弟弟小时候偶尔半夜尿床,奶奶说他的“肾”太弱,会买一些荔枝干煮汤给弟弟喝,没几次弟弟就不尿床了。对我而言,奶奶就是一个医生。她做的草药汤,闻起来很香,喝下去暖胃。那时我并不认为“生病”是件痛苦的事。我觉得发高烧、拉肚子是逃学的好借口,生病了能喝甜甜的咳嗽药水,吃爸爸给我做的病号饭,最糟的也只不过是拔罐刮痧以后在身上留下的几道红印。
我第一次了解生病的痛苦是在我十四岁的那年。我的母亲因为肺部生了一个鸡蛋大小的瘤不得不手术。当时医生怀疑她得了肺癌,这消息使全家痛苦绝望,妈妈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父亲先把年老的奶奶送到乡下,想尽办法借到了做手术需要的钱。我还记得妈妈流着眼泪强“笑”着对我说,万一她不能从手术中醒来,要照顾好弟弟,担起家务事,更要好好学习,以后当个医生,有本事去拯救像她一样的患者。中国四十年前的医疗水平非常有限,有些人手术后从没能离开医院,也有人就死在了手术台上。我那时十四岁,开始知道有些“病”是会让亲人生离死别的,我很担心妈妈,跟着奶奶去庙里求药师佛祖保佑母亲,那时我真希望自己已经是一个医生!幸运的是妈妈手术中取出的肿瘤并不是恶性的,全家如释重负,但我从此也对“疾病”开始有了惧怕。
中学毕业以后,十七岁的我被下放到农场成了农民,成了300多人连队的一名小领导,在一片荒芜的海滩边开河道、挖沟渠,每天的工作体力消耗很大。新围垦的连队住的是芦席棚,喝的是咸涩水,盐碱地上寸草不生,只有一望无际的芦苇在海风中刷刷作响。艰苦的生活条件、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以及严重的营养缺乏使很多人生病了。记得有一次连队的职工中发生了霍乱,为了防止流行病的传播,我们与世隔绝般的在防疫区生活了数周。我看到的瘟疫吞噬着年轻人的生命和健康,往日里生龙活虎的职工上吐下泻,腹痛得满地打滚,病恹恹地耷拉着脑袋连话也讲不出来。那时医务室的卫生员让我由衷地肃然起敬,仿佛只有她才是我们唾手可及的救命稻草。偶尔露面的医生,在我心中简直成了生命之神。我这才理解,母亲为何一直希望我成为医生!
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日渐衰退,眩晕头痛发作频繁,经常晕倒在开河工地,有一次从近十米的河堤上滚下,让锋利的河锹割伤了右额和眉毛,缠着满头的渗着血的绷带,被送回城里进了急诊室。拍片验血一阵折腾也没有检查出发病原因。有些医生认为我的脑动脉可能有畸形,有些人觉得可能是癫痫症或是美尼尔症,可是没有人能够确诊我的病。当时二十岁的我整天头晕、恶心,有时候还会昏厥。父亲带着我去了许多著名的大医院看病,拜访了不少名医,吃了种种西药,对于一个经济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每次的诊金和药线常常让父母捉襟见肘。我的父亲带我求医三年,可是他的努力并未见效。
1977年我二十二岁,中国政府恢复了高考制度。我通过努力考取了上海中医学院,离开了工作了三年的农场,开始了我成为中医医生的道路。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每天学习超过十四个小时,很少休息。我的未经确诊的头痛和晕厥依然时常困扰着我,让我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我常常在课堂上、校园里晕倒并失去知觉,这让周围的人不知所措,更让我觉得十分难堪。因为生病,我的内心非常自卑,我的青春时光也因此变得压抑沉重。我把自己的所有时间倾注在学习中,尽管那时的记忆力不够好,但我认为自己可以“笨鸟先飞”。我鼓励自己要坚强、不浪费青春的时光。我不想落后,更不愿意自悲自怜。这也是我今天理解和重视青春期体智疾病调理和治疗的重要性的原因。我知道青春期的病痛不仅仅伤害他们的肉体,还扭曲着他们的心灵,有些疾病可能对青少年今后的生活、职业和自信产生严重影响,即便是像便秘、肥胖、抑郁、痤疮、脱发、口吃和身体疼痛这类无关轻重的健康问题不得到及时治疗,也将会影响他们将来的生活和事业。
当我读大四的时候,一个教中医伤科的老师发现我直立后晕厥,以指压方法在颈部做了几处检查,认为我的晕厥由颈椎病变引起。果然,经X光检查后证实了我的颈椎椎间孔有一处狭窄。当头颈转到某个位置导致了椎动脉缺血,晕厥就会发生。之后,通过近两年的针灸和推拿治疗,我的病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直至痊愈。那改变了我一生的治疗使我决意要成为一名中医医师,去帮助那些和我一样生病的人,那年我二十五岁。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医院不同科室如内科、外科、妇产科、肿瘤科、骨伤科、急诊室等做了两年住院医生。然后我考回母校攻读中医硕士、毕业后受聘于上海中医大学各家学说教研组当了助教,并有幸考取了名老中医大家裘沛然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1990年元月,我在来美前夕去裘沛然先生府上辞行。裘老赐我“鸣岐堂”作为行号,鼓励我做一只越洋之鸟,携针衔药,不辞辛苦,鸣岐黄之学于西洋,播杏林春苗于彼岸。我于1990年初来到纽约,通过考试获得了纽约州针灸执照,于1991年成立了鸣岐自然保健中心。那时的美国民众还不熟悉中医,我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来向患者和他们的西医医生来宣传有关中医的知识,使他们了解近年来中国开展的对中医针灸的科学研究进展。我与天才老爹Bill Cosby在ABC电视台Riges’s & Kathey Lee 的中医节目在美国引起轰动,由此有机会开创了美国许多影星、歌星、市府和华府官邸等名流的中医市场。鸣岐堂每天接待40至50号病人,忙的时候有时会有70多号病人,以针灸和中草药对子宫肌瘤、带状疱疹、牛皮癣、退化性关节炎、更年期综合症和过敏症等等开展中医针灸的临床研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随着美国民众对中医针灸的了解和接受,中医疗效逐渐被肯定,也越来越受欢迎。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来自于主流医学对中医的了解不够全面,也来自于中医师专业技术质量不够稳定以及缺乏统一的专业标准等因素。这是我们需要以不懈努力去解决的问题,以此逐渐赢得西医主流医学的理解合作,团结更多的美国针灸师和西医针灸师的力量。
我年轻时候受益于中医,她给了我健康,也让我决心献身此业。但我也是西医疗法的受益者。我曾在就读研究生时患有心肌炎,频发性的心律不齐,必须依靠西药来控制心脏的衰竭,并以中药巩固改善心脏功能。由于心脏扩大,二尖瓣关闭不全无法维持妊娠,我失去了第一个孩子。来美国后,我40岁时再次怀孕,在严格的心脏监护中度过了怀孕期。虽然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引起的水肿使我重了70磅,但我还是在心脏专家、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妇产科医生的帮助下,做了动、静脉切开插入心脏导管,经剖腹产生下了我的女儿。如果不是美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临床成果,我也许不得不接受第二次流产。
西医和中医虽然对于疾病的理解和治疗方法不尽相同,但我认为无论用哪种方法治疗疾病,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中医有着四千多年的历史,她基于临床经验代代相传的历史背景,其理论不像西医学那样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我们这一代中医的责任是,用合理而科学的方法来论证中医的临床功效,结合中西医疗法的长处来造福民众。
建立这个网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来到美国以后,我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从来没有离开过诊所,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写作。1997年我怀孕时每天在心脏监护病房被迫休息,这才有机会拿起笔开使准备资料,历经六年直到2004年才把网站建好。2015年将是鸣岐成立的第25个年头,因为诊所业务的扩大和公司结构的变更,我们更新了网站的内容,希望她提供的信息更全面、更受用,也是我们在庆祝鸣岐25周年纪念日时对多年相信和支持我们的患者的回馈。我希望我们的网站能符合查询者的需要,让我的文字关爱就像我在诊所的工作一样,可以为你们的健康提供有益的信息和服务。
我爱你们每一个人,并真诚地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美满。